2021年6月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史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之邀,在文华楼东区1106教室进行题为《档案发现与清代政治史研究中的“自我解构”》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陈鹏副教授主持,本校师生六十余人参加。

讲座伊始,刘文鹏教授提出了两个理论问题,抛砖引玉,即“历史可以被认知吗”“历史如何被认知”,进而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清朝留下的历史档案非常丰富,是研究清代历史特别是政治史最重要的资料。与会典、实录等资料反映的平面化政治制度不同的是,历史档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动态的视角,带着这一视角会发现,制度形成往往是政治变革的结果和体现。要正确认识某种政治变革和制度的真实面貌,需要通过档案史料,在对以往认知的自我解构中,形成对历史实际状况的场景化认识。
首先,刘文鹏教授指出,百年来,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与利用是清史研究获得不断进步重要因素,清代中央档案的利用是大陆清史学者代际更替的重要学术标志,档案的充分利用推动了清史研究重心由台湾向大陆地区转移,促进了清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化。
而后,刘文鹏教授以军机处研究为实例举证,说明档案对清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关于军机处的研究主要围绕其成立时间、成立原因、实际作用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军机处的重要材料主要有梁章钜《枢垣记略》、叶凤毛《内阁小志》、吴振棫《养吉斋丛录》、王昶《军机处题名录》、赵翼《簷曝杂记》、《清史稿 军机大臣年表》、《清史稿 职官志》。对于军机处的成立时间,目前学界大致有雍正四年说、七年说、八年说等三种说法。对于军机处、军机大臣的实际作用,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军机处到底是只供撰述、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秘书机构,还是军国大政罔所不揽的核心权力机构。关于军机处的职掌、运行情况,史料中语焉不详,基本持相似说法。迄今为止,很少有能够直接证明军机大臣在决策国家军政事务中到底如何发挥作用的材料。而刘文鹏教授则通过议覆档等档案资料,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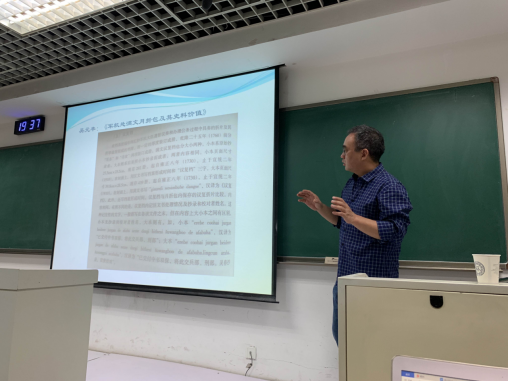
接着,刘文鹏教授以“为何在新疆建立驻防体制”为中心,讲述了档案与军府制度认知的再构建,以伪孙嘉淦奏稿案的相关问题研究为例,说明了并非所有档案皆可相信,又以马戛尔尼访华事件为例,借助英国学者沈爱娣的论文《<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及有关传统中国对外关系之观点在二十世纪早期的形成》,谈及档案的再发现与历史认知的重构。
刘文鹏教授指出,档案史料的编纂者可以决定保留哪些档案和排除哪些档案,档案整理影响了学者对马戛尔尼访华事件的判断。礼仪其实并非乾隆皇帝关注的重点,在清王朝所有文献的记述中,马戛尔尼使团都被看作防务问题,重点放在军事准备和对英国人在广东贸易的管理上。那么,为什么礼仪问题会被提炼出来,就非常值得关注。一直到辛亥革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的礼仪问题一直都是西方关注的焦点。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埃德蒙·贝克豪斯爵士和约翰·奥威·玻西·布兰德就出版了一部关于清朝历史的著作,书中收录了《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的完整翻译。该书把乾隆敕书呈现给公众,而一些人便将这道敕书看作中国人傲慢的罪证,进而为英国侵略中国辩护。1914年,两位居华英国作家把乾隆敕书的英译本收录进他们编写的清朝野史,中国学者正是从这本英文著作中摘选出《乾隆皇帝谕英王乔治三世敕书》,乾隆在敕书中的愚昧和自满正好应和了民国革命。民国时期,许宝蘅与助手们一起编纂了《掌故丛编》,收录了一批经过挑选的档案文献,将清王朝描绘成一个面对正在崛起的西方力量,既无知而又被动的王朝。清朝官员一方面对礼仪细节表现出过度的关注,一方面又对他们所面临的军事威胁毫无察觉。该书旨在利用这些档案制造出一个批判清王朝的新历史,指责被推翻的清王朝分不清礼仪和现实孰轻孰重。

最后,刘文鹏教授对培养档案利用与解读能力进行了总结,提出我们应具有明确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档案的全面认知、扎实可靠的档案资料使用能力与精炼的写作能力。随后,在交流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提问,刘文鹏教授一一予以详细解答。讲座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同学们对刘文鹏老师和陈鹏老师表达了感谢,本次讲座顺利结束。

(王诗萱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