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晚七点,我的恩师顾章义教授不幸离世,享年88岁。噩耗传来,悲由心生,不禁回想起我俩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的母校—中央民族学院坐落于北京西郊,现在叫中央民族大学,它是我国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和研究民族问题的最高学府。我18岁走进这所大学的历史系,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四年时光。那是孟浪却不失纯真的年龄,那是懵懂但追求理想的韶华,这个校园给我留下了太多记忆,也是在这里我结识了顾章义教授,并开启了我俩长达40余年的师生情缘。
说来也巧,我与顾先生的交往颇有戏剧色彩,大概是大二时,我们的专业基础课—世界近现代史老师换成了顾先生,我依然留有初次见到他的印象:个头不高,人挺瘦,身着一件深蓝色解放装,一口带有明显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不急不缓,一板一眼。“唉,也是个普通人嘛”,我在心里暗暗思忖,但没想到很快我就栽到了这位普通人的手里。
期末考试我这门课勉强及格,刚刚60分,当然得60分的不是我一个,还有几位。大家觉得评分太严,应该去系里给老师提意见,我却没有这个雅兴,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提意见纯属多余,60分意味着这门课已经过了。几天后我在校园里偶遇顾先生,他问道:“那天提意见你怎么没去?”我笑着回答:“60分说明没学好,以后应该努力”。他叮嘱我:“这是专业基础课,要下点功夫。你以后有不清楚的地方就去找我,去家里去办公室都行”。从此,顾先生之于我从一位普通的授课老师转换成了生命中的领路人。
那时他的家很小,只有两间房子,一间住着两个儿子,另一间是夫妇二人的卧室兼书房。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过去,口头上请教问题,实际上去老师家蹭饭吃。顾先生一般让我先看会书或报纸,自己或师母陈瑞萱去厨房做饭,不一会就会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汤面,面里肯定有一个荷包蛋……
当然除了蹭饭吃,我也会请教一些问题,问答间渐渐深化了我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他对我系统地学术训练则始于大学四年级,那年我选择当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加纳共和国的缔造者克瓦米·恩克鲁玛作为研究对象和毕业论文题目,并请顾先生当我的指导老师,全身心投入到论文写作之中。有一天,顾先生给了我一篇他刚刚发表的论文《评非洲部族说》和讨论民族概念的文献目录,让我把这些文章都读一读,总结一下各派观点。
我至今记忆犹新,中文“民族”一词始见于辛亥革命前,其概念是指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们共同体,在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著作中,可以根据具体语境将其细化为:1、广义的人们共同体,包括氏族和部落。2、阶级产生以后各个时代的人们共同体。3、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也就是“现代民族”,其经典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们”。4、“现代民族”概念确定以后,“部族”一词专指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人们共同体。
顾先生通过这种训练,让我了解概念并养成正确使用概念的习惯,由此受益终身。数十年后我俩在一起讨论大学到底学什么问题时,我告诉他自己的体会是学习治学的方法。他听完我的回答,两眼含笑,微微点头……
毕业论文他指导我从二战后非洲历史背景入手,由远及近,由高到低,不拘泥于一时一事,从宏观上把握加纳民族独立运动及恩克鲁玛的个人作用。顾先生曾引述列宁的一段话指导我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使我走入社会后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没有人云亦云,失去判断是非的标准。
我的毕业论文也告别了60分,以优秀的成绩在自己离校几个月后全文刊发于《非洲历史研究》期刊,这要归功于顾先生的指导和举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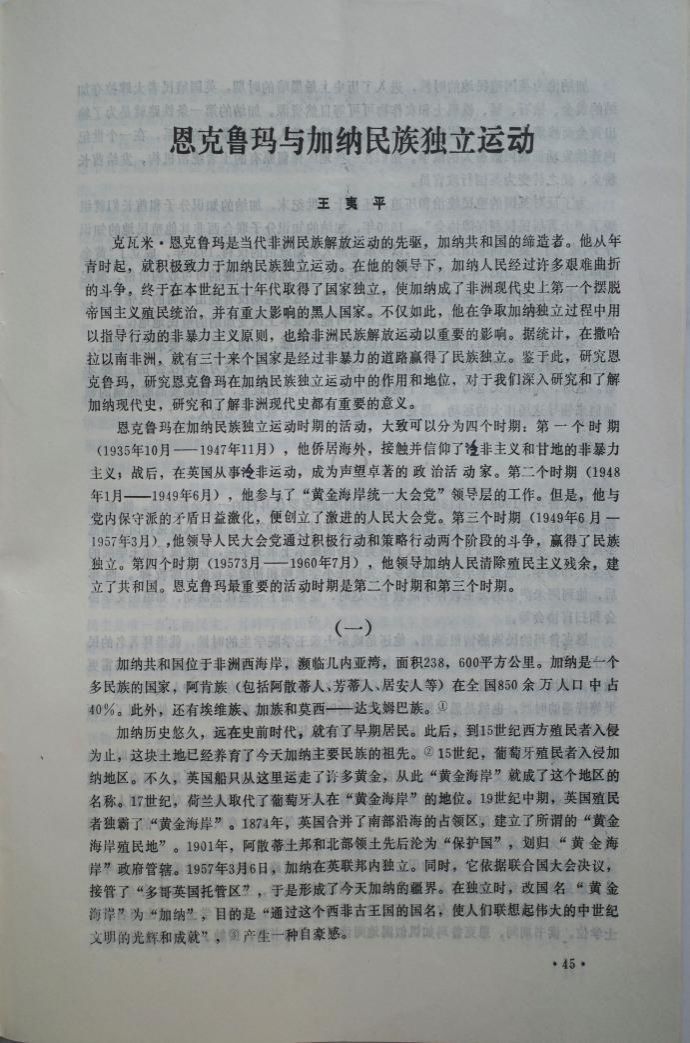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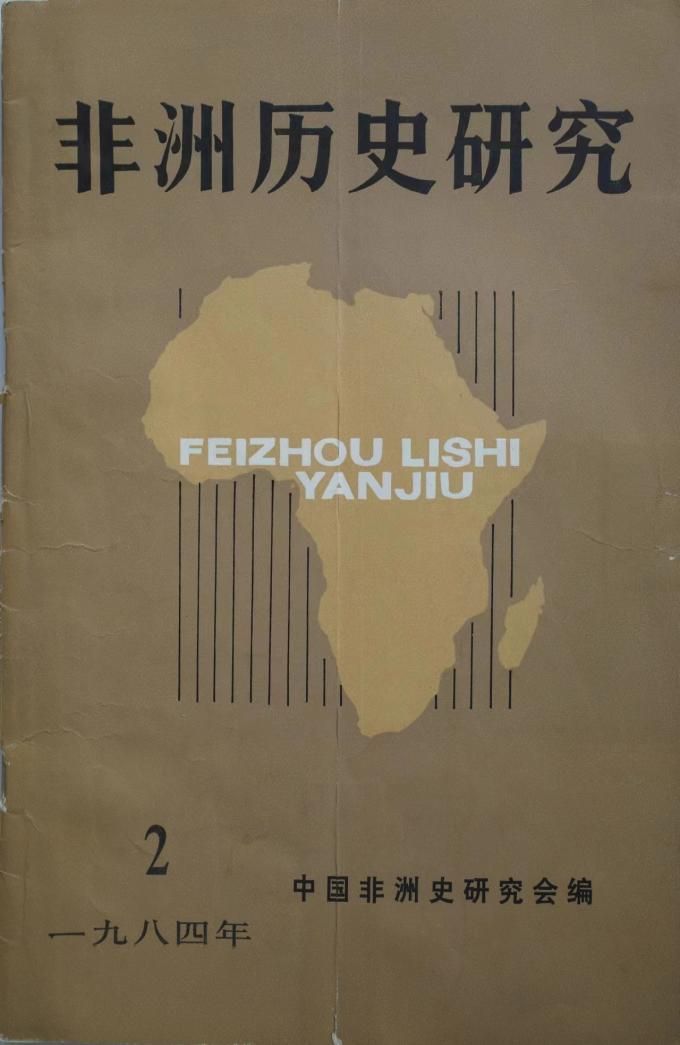
作者大学毕业论文
第二年我又回来了,到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阿拉伯语。我仍然时不时到顾先生家蹭饭吃,他领着我拜访了一些学界宗师,如林耀华教授、纳忠教授等,还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大约是1986年秋季的一个中午,刚从食堂吃完饭回到宿舍的我就碰到了顾先生,他骑了个自行车从魏公村专程到北大找我,一见面就高兴地说:我带研究生了,你进修结束后直接考我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吧!
聊完天我把先生送到了校门口,他骑上自行车又汇入了中关村滚滚的人流之中。望着先生渐渐消失的背影,我忽然产生了好奇心: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又经历过什么事情使之甘当阶梯,举起自己的学生?
顾先生1936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一个贫苦的农家,他出生当年父亲便因病去世,留下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靠耕作几亩薄田艰难度日。到了入学年龄,他在外公的资助下上了村小学,学习之余还要帮家里干点农活。在宗法制盛行的旧中国农村,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遭人欺侮是必然的事情。顾先生有个叔叔抽大烟败光了自己的家产,他把弄钱的目光又盯在了寡嫂身上,硬说嫂子的田有一块属于他,悄悄把这块田和收获的庄稼卖给了一个恶霸。顾先生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母亲坐在门口哭泣,进屋一看,家里被恶霸带人砸得乱七八糟,庄稼也被抢走了,幼小的他从此明白了什么是压迫、什么是以强凌弱!
1949年母亲再也承受不住生活的重压,撇下一对儿女撒手人寰,家里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上初中的顾先生也面临着辍学的窘境。好在解放了,学校通知他:困难学生可以申请免交学费,他因此得以继续学习。1950年他初中毕业考入浙江省立台州中学高中部,高中期间他不仅享受国家的甲等助学金,还结识了对他人生观塑造产生重大影响的恩人吴全韬先生。
吴先生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是台州中学高中部的语文老师,也是顾章义的班主任。吴先生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耿直、善良、爱才,他特别欣赏顾章义身上那种刻苦、聪慧和节俭特质,对这个失去双亲的学生青睐有加,鼓励他不要因为贫穷就放弃追求理想,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之中。由于品学兼优,顾先生被同学们推举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和台州地区学生会组织部部长。
1953年他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今吉林大学),临行前吴老师拿出自己的毛衣送给他,叮嘱道:“东北的天气比浙江冷多了,你要多穿点才能抗寒”。还告诉他:以后每两个月都会给他寄5元钱让其零花,一直到大学毕业为止。重如泰山的师恩啊!一个中学教师每个月只有区区几十元工资,要养儿育女,还要支撑家庭的其它开销,硬是从牙缝里挤出钱来资助了自己的学生。
1957年顾章义大学毕业后被选拔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但这时吴老师却失去了联系,任他百般联络就是没有回音,后来他多方打听才知道恩师被划成了“右派”。一切尽在不言中,吴老师害怕自己的“右派”身份殃及顾章义的政治前途,忍痛与他断绝了往来。距离可以阻拦交往,但息灭不了学生对恩师的思念之情,顾章义对那件毛衣格外珍惜,睹物思人,破了就补,一直穿到六十年代末无法再修补时才依依不舍丢掉。
1979年已经失联了20多年的吴全韬老师忽然给顾章义来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属于错划“右派”,现在已摘掉了“右派”帽子。随后吴老师所在单位又正式函告历史系:你单位顾章义的高中语文老师、班主任吴全韬属于错划“右派”,现已摘帽。听到这里我久久无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个道无论有多少种解释,它必然蕴含着选贤荐能的伯乐精神,堂堂正正立于天地间的师者垂范,推已及人的仁爱之心,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这些价值观无论中国处于何种境地,都一直流淌在民族的精神血脉里。
这些年民间有“四大害”之说,将老师归入其中的“眼镜蛇”,媒体还时不时爆出男老师上了女学生的床,女学生钻进了男老师的被窝等丑闻。每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有一种不祥之感:中华民族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教师,多么神圣而崇高的字眼,肩负着百年树人的重担。如果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烂掉了、失守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有未来吗?

吴全韬先生
吴全韬老师对顾章义的期许和付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到民院工作后,虽历经那个年代各种政治运动,岗位也在校内几经变动,但始终以世界现代史和非洲史作为研究重点,其学术地位可以从他前后发表的两篇论文中看到变化:1963年刚27岁的顾章义就在历史学人眼中圣殿般的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非洲的觉醒》,在学术界崭露头角。2009年建国60周年时他代表中国非洲学界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期刊《西亚非洲》上又发表长篇论文《当代中国与非洲》,对中非之间新型国际关系进行回顾、总结与展望,其权威性不言而喻。而权威的背后是他几十年奋斗的足迹和累累硕果,他已经从一个青年教师成长为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本科生和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学术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中国亚非学会和民族学会理事,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92年顾先生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实地考察非洲,时间长达一年,弥补了过去缺少实地踏勘的缺憾。他著述200余万字,荣获校级奖励一次,省部级奖励二次,国家级奖励一次。他教书育人,本硕博桃李满天下,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社科和外交领域的栋梁之材。


顾章义教授在非洲考察
而我—他最在意的学生却与他期待的目标渐行渐远,不仅没有报考他的研究生,最后还脱离了文化界。我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位自己敬重的长者,每到北京肯定第一时间去探望他;每次相见我俩都交谈甚欢,顾先生还会跟我聊起学界话题,告诉我他们的研究进展和各种观点等。好在我虽然离开了文化口但没有丢掉读书和思考的习惯,交流不存在障碍。交往了40多年,他的性格一如往昔:说话不急不缓,既不当面夸你,也不当面批评你,不同意你的观点时也是点到为止,给你留足面子和里子。
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有一天忽然被打破了,那天他的长子无意间告诉我:“那年我爸得知你离开了文化界的消息后,彻夜未眠,在客厅里不停地踱步,一边转圈一边喃喃自语:可惜了、可惜了……”
听到此话,我当时就愣住了,万万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老师还对我抱有如此之大的期许!这件事儿就像一把榔头敲醒了我,促使我认真思考余生的路应该怎么走。
我喜欢阅读、写作和旅行,擅长思考,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如果将这几个方面合而为一,给读者讲述大西北的人文故事,不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吗?
大西北辽阔而壮美,苍凉而厚重,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海运兴起之前是中国与欧亚其它文明沟通交流的杻纽地区,有看不完的景点、讲不完的故事。湖光山色固然有观赏价值,但它背后的人文故事更值得聆听,因为这些故事隐含着中华民族步步壮大的基因密码。
讲好大西北的故事并不容易,我国文献三大源流正史、方志和家谱内容并非都是信史,需要甄别、考辨、去伪存真,需要将具体事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才能拨云见日,这个时候作者的学术道德和学术功底尤为重要,可以说曾经受过的学术训练和养成的学术习惯决定了你笔下的文字是否可靠。
我一直认为学者的另一个社会责任是在学术象牙塔与广大受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心相通,则情相融,这样学术才能发挥启迪民智,引领未来的作用,才会具有更持久的生命力。
文学与学术交融所产生的人文游记是我正在尝试架起这座桥梁,但能否成功有待于时间地检验,因为有价值自然会流传下去,没有价值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自己问心无愧而已。
我第一篇游记完稿后专门打印出来送顾先生审阅,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多年不动笔了,现在还行不行没有把握,想听听老师的意见。二是以此来安慰老人家,告诉他我已经回到了文化的轨道上。没想到80多岁的顾先生爬在中国地图上一个个核对文章中出现的地名,又打电话让我再去一趟家里,当面告诉我哪些语句不恰当,应该如何修改等,并给出了分数:80分。
望着先生日渐消瘦的脸庞和认真的模样,我的双眼湿润了,仿佛看见了站在他身后的吴全韬老师,脑海里直接蹦出两个字:传承,这就是师道的传承。“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立言书写人生是顾先生对我的期待,也是我正在走的路,我相信在当代中国认同这种传统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会越来越多,最终将汇成汹涌的洪流与金钱至上的享乐主义思想发生正面交锋,并凯旋而归,继续撑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
文:王夷平(历史系80级学生)
初审:陈鹏
复审:彭勇
